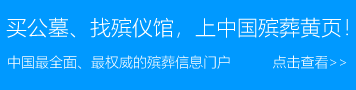土家族的“跳丧舞”,歌乃高亢欢快之曲,舞系豪迈雄健之风,无悲痛哀伤之感。土家人“跳丧”,讲求的是“欢欢喜喜办丧事”,“高高兴兴送亡人”。他们把丧事称之为“白喜事”。老人去世后,为老人去世举丧,办得越是热闹红火,就越是有面子,有孝心。表明土家族对“死”积淀着古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即灵魂不灭,生命永恒,生与死是生命存在的不同形式的自然转换,死亡是旧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生与死都是人生的必由之路。因此,土家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是乐观的,尤其是认为老人去世是“顺脚路”,是衰老多病的躯体重新获得生命活力的开始,所以办老人丧事“丧”而不“哀”,“哀而不伤”,气氛十分热烈,歌舞成为必要的表现方式,甚至男女调情的俚词亦不避讳。举丧实质上成了礼赞生命、祝福新生的一种特殊的祝福仪式和超度来世的宗教仪式。这种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人生观萌芽生成于土家族先民原始的灵魂观念,千百年来一直浸淫在本民族的巫文化之中,虽多有唯心成分,但又始终贯穿了热爱生命、追求幸福平安、积极进取的主题,并对民族的生存繁衍产生了重要作用。这种观念,渗透在土家族特有的丧葬仪式活动中。“昨日看见亡人在,今日已经进棺材,三日未吃阳间饭,四日上了望乡台”,“歌郎送出门,庄子返天庭”(“撒尔嗬”歌词)。土家人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在继续活动,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灵魂存在并游离,因此才有“开路”、“回煞”等丧仪现象。“回煞”等现象表明活人同死人的灵魂仍在一起活动。“灵魂不死 ”是 “跳丧舞”这种祭悼形式产生和形成的心理基础,这种观念虽然是人类原始社会的共有现象,但土家族跳“跳丧舞”的表现方式则是独特的土家族的跳丧是对死亡的一种阐释“灵魂不死”、“死后脱生”的观念使土家族人形成“死是福”的生死观。古今中外一般都把死亡看作悲惨可怕的结局,佛教和基督教宣扬死亡就是进地狱;道教追求长生不老, 都力图超越死亡。土家族对待死亡并没有阴间世界的那种阴森恐怖,也没有佛教中所描述的那种空寂。土家族认为死亡是人转变为另一种新的生命,即死而脱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亡,到另一个世界上是生存。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生命的开始,生而死,死而生,死亡好比新生婴儿降世一样,理所当然可喜可贺。因此,土家族人死后跳绕棺、“撒尔嗬”时,“合族不悲”,哀而不伤,相反气氛热烈,似乎是歌舞聚会,没有庄严肃穆的氛围,这些似乎自相矛盾不相协调的现象,正是土家族“死后脱生”和“死是福”的生死观念的体现,同时也是人间离别的依恋。土家族在清代改土归流后,虽然受到汉文化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的强烈冲击,民族文化本身消融较多,土家族一些独特的丧葬习俗却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传承下来,正是因为这些习俗尤其是跳丧现象,实质上是信仰与理性的产物,具有一种“准宗教”功能。这里要指出的是,跳“撒尔嗬”时,“合族不悲”,哀而不伤,是指丧葬之前。临葬之际,开棺供亲友瞻仰最后一面,此时众人悲伤,乃至恸哭,史书记载为“即葬反哭”。这是生离死别,哭之情理自然,并与跳丧悼念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再现民族文化源流的历史轨迹这一点尤其在绕棺和跳“撒尔嗬”的祭悼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绕棺、跳“撒尔嗬”是鄂西土家族的主要丧祭形式,主要在清江流域及其附近一带流传,其舞蹈动作和唱词也较为古朴,可以认为它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带的古代巴人及其后裔创造的一种文化。从跳“撒尔嗬”流传的区域与巴人迁徙活动的路线来看,古史记载巴人为廪君之后,源于清江的武落钟离山,是一个勇猛强悍的部落,曾在清江流域靠渔猎生息了很长一个时期, 并在清江上的盐阳、夷城等地建立过原始部落联盟,以后沿清江入川建立巴国。跳“撒尔嗬”正是在长阳、巴东、建始、鹤峰、恩施的清江沿线流行。魏晋南北朝时就有史籍记载这里的土民:“父母死……打鼓踏歌,亲属饮宴舞戏。”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叫啸以兴哀,“蛮夷信鬼尚巫,伐鼓踏歌,以祭神。”在鄂西生息过的巴人,死了老人,阖族不悲,且把它当作欢乐的喜事,举办“白喜”,“伐鼓踏歌”,“其歌必狂,其众必跳”,合族举庆 ,以祝其功,这在当时当地的汉人是不会这样办的,就是当时当地与土家相邻的其它少数民族,他们虽然也有歌哀的形式,但与土家作为“白喜”来跳丧鼓庆贺还是不同的。从跳“撒 尔嗬”所透射出的崇拜内容看,表现了强烈的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意识。原始丧鼓歌保存下来的已经很少见了,但在流行的一些长篇歌词中,仍然可以发现赞扬土家先民开疆辟地创业和原始图腾的印记。“走进门来抬头望,桑木弯弓挂墙上”,这显然是古代土家族先民渔猎 和征战生活的影子,因为桑木弯弓是渔猎的必备工具。“三梦白虎当堂坐,白虎坐堂是家神 。”(“撒尔嗬”歌词)这是土家族的图腾崇拜。清江流域土家族信仰“先民在上,乐土在下,向王开疆辟土,我民守土耕稼”(“撒尔嗬”歌词)表现对土家族共同祖先向王天子(传说中的廪君)的崇拜。从绕棺、跳“撒尔嗬”的摹拟动作形象看,凤凰展翅、犀牛望月、牛擦痒、狗吃月、燕儿衔泥、幺妹子姐筛箩、猛虎下山等舞蹈动作的命名和表演,无一不形象逼真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这些舞蹈动作是巴人对他们祖先劳作、生活和娱乐的高度概括,如“凤凰展翅”,二人背对背,双臂展开,上下扇动,恰似凤凰展翅欲飞,其动作含蓄,隐喻力强。擦痒 ”,二人背靠背,双手叉腰,左右相对擦晃,腰胯以下作慢幅度颤动,稳健明快。“燕儿衔泥”,是一个高难度动作,一人丢一手帕(或其它物件)下地,另一人叉开双腿站立,随着鼓点的急骤加快,慢慢弯下腰,但双腿要直,最后以嘴近地衔物,双手后翘作燕儿翅膀扇动状,反复数次。最为壮观的是“猛虎下山”,那是在午夜过后,酒醉舞蹈,人们疲倦欲困时,舞者跳着跳着,忽听鼓点一变,二人中的一个猛然跳跃腾空,一掀舞伴,然后两人躬身相对逼视,忽而击掌、撞肘,前纵后掀,一跃一扑,模仿猛虎扑食的各种动作,口里还发出一阵阵虎啸声,最后一人被另一人挽着从头顶上后弓翻跃过来,动作形象逼真,给人以其祖先为虎的粗犷雄壮的崇敬感受。其他动作和格式,有不少是模拟表演他们的先民掷镖渔猎、 厮杀械斗的动作,如“打上二十一”中的击掌,“幺姑姐筛箩”是土家生产和生活、娱乐等事体的表演,这些都是土家族习俗浑朴、淳厚古雅的写照。
死亡意味着家族成员减少,对付自然和社会力量的削弱,整个家族和民族都掀起感情的波澜,引起心灵共鸣,“人死众人哀”,表现共同的民族生存忧患意识,远亲近邻无亲无故者都“不请自然来”,甚至生前有冤有仇者,“生不记死仇”,化干戈为玉帛,大家“一打丧鼓二帮忙”,“打不起豆腐送不起礼,打夜丧鼓送人情”,齐心协力帮助料理死者后事,互助互爱,团结一致,表现共同的民族团结合作的意识。乡邻借丧祭活动,张扬吉利,祈祷祝福:“走进门来抬头望,孝家坐个好屋场”,“亡者归葬后,孝家万年兴”(“撒尔嗬”歌词),所以土家族的丧祭活动,不仅仅为了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生者,它表现了民族共同发展意识。同治《巴东县志》云:“而哭友一节可谓独得,缔交之至情,虽古人雅道,不足过矣。”这是名副其实的。
土家族丧祭活动是土家族天然的社交聚会,“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南方和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跳一夜丧鼓送人情。”(“撒尔嗬”歌词)人们借此机会交流感情,传播信息,相互的联系扩大和深化,融合程度加快加深。土家族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居住分散,隔绝闭塞,通过丧祭活动,成为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土家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心理素质,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地域的形成、融合、发展过程中更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是土家族地缘民族共同体形成不可缺少的一环。它表现了土家族的群体意识,民族生存忧患意识,团结合作意识,共同发展意识。在土家族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一种有着丰富实在的深刻内容的极为稳固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积淀成为土家民族的凝聚向心力,实质上是土家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土家族丧葬活动成为土家文化传承的载体
丧葬过程中的歌舞活动在口耳相授世代相传过程中,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史前社会生活事象,对于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
土家族社会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在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丧祭活动又吸收消化了汉族文化,“混沌初开出盘古,浑身一丈二尺五,手持开天辟地斧,劈开中央戊巳土,人凭天地号三皇,天皇地皇与人皇;轩辕皇帝织衣巾,神农皇帝尝百草……”(“撒尔嗬”歌词)“天地相合在佛祖,日月相合生老君,龟蛇相合生黄龙,姊妹相合生后人。”(“撒尔嗬”歌词)其他诸如丧歌中的《姜子牙》、《桃园三结义》、《杨家将》等,都为明清时期创作,是吸取消化汉文化后的产物,不仅保存和传播了土家族原始文化形式,而且通过吸收消化汉族文化,创造了新的具有土家特色的文化,尤其是“撒尔嗬”容量大,兼容并包,表现力强,包含神话、传说、历史、诗 歌、民俗、伦理等土家族社会生活事象,远远超过其歌舞艺术本身范畴,成为土家族多方面文化传承的载体。
土家族跳丧舞又叫绕棺、打绕棺、丧鼓舞,是巴人在两千年前传承下来的民间歌舞。老人逝世,停灵枢于中堂前数日,亲属邻里前往吊唁。入夜,打鼓踏歌,通宵达旦,以增热烈气氛,谓为亡人人解寂,慰新属节衷。土家人热爱跳丧舞,”听到鼓声响,脚板就发痒”。跳丧舞的特点基本与土家族的摆手舞相似,手脚同边,舞姿豪放,动作平常,舒缓着节奏强烈的打示波器乐,舞者边跳边唱,唱腔多用假嗓音,近似喊歌。男女老少齐跳,舞蹈词汇健康,一般以歌颂死者生平事迹,歌唱扶育之恩以及劳动生产方面的内容为主体。土家跳丧舞集歌、舞、吹、打为一体,是一种综合性的民间艺术,是一种民间祭祀活动,表现了土家族人对祖先的崇拜和敬仰。
少数民族的特殊丧葬习俗-土家族跳丧
| 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