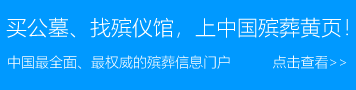近年来,围绕“有尊严地死”(下文简称“尊严死”)的议题引起了学界、相关社会组织以及普通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不少专业人士提出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尊严死、消极安乐死(不给予或撤除治疗)、(积极)自愿安乐死和安宁疗护等措施。如何理解尊严死再次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
尊严概念在生命伦理学中的大量使用,源于20世纪70年代关于过度医疗和死亡权的讨论,这一讨论始于1975年美国卡伦(Karen Quinlan)事件,首次采用了“death with dignity”。随后,“有尊严地死”在人们讨论重病患者或临终患者的生存状态时经常被提及。长寿是构成人类幸福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世世代代孜孜以求的愿望。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医学在帮助人类摆脱疾病困扰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烦恼。例如,临床医疗上的体外循环装置,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心肺运动的功能。该医疗器械的诞生,意味着一旦某人心脏跳动和呼吸停止,如果及时运用这些设备,仍然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这个人的生命体征。也就是说,技术可以使这个人“一直活下去”,无论其生活质量如何。长期以来,人们片面地理解医学“治病救人”的神圣使命,认为“抢救”是医学的使命,“放弃”就是医学的失败。客观上医学技术的便利和主观上对“救”的片面理解,令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即便承受着更多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也只能“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地“活着”。
这种过度医疗现象的广泛存在,不仅给患者本人造成折磨和痛苦,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不是对生命的挽救,而是对生命的摧残。于是,有学者指出,与其说医学技术是在延长寿命,不如说是在延长死亡。在这一讨论中,人们经常会提到尊严死的权利。尊严死的权利运动正是对那种无意义地延长死亡的治疗方式的抗议。这一口号的提倡者们认为,过度治疗是对生命尊严的严重侵犯。
上述讨论促使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文件,在不同程度上保障个体自主决定死亡方式的权利。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人类在走向死亡过程中,在决定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呈现出几种形式或选择。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背景、术语使用习惯的差异,尊严死、自愿安乐死、不给予或撤除治疗(消极安乐死)、安宁疗护、临终关怀等词汇之间的边界并不清晰。不同学者在阐释、讨论这些文件规定和相关问题时的表述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尊严死在不同的文献、不同的语境中所指代的死亡方式也呈现出差异,尊严死的内涵变得愈发含混不清。
这种混淆给人们的实践生活,尤其是在推动尊严死的相关活动上造成了很大程度的障碍。例如,在目前安乐死依然面临伦理和法律上诸多争议的社会背景下,如果尊严死意味着安乐死,那么推动尊严死的相关工作必然也会受到诸多阻碍。正因此,业内人士强烈主张区别尊严死和安乐死。在他们看来,安宁疗护和缓和医疗所指向的死亡方式才叫尊严死。这是一种自然的死亡方式,既不加速也不延缓死亡时间,相关的措施旨在解除患者的痛苦和不适。在这个意义上,它区别于涉及积极致死行为的安乐死。毋庸置疑,在目前安乐死存在诸多争议的社会环境下,严格区分尊严死和安乐死在推进安宁疗护和缓和医疗实践,保障患者死亡权利方面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然而,笔者更愿意将这种区分理解为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为推动尊严死运动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当我们从理论上反思尊严概念的内涵,并尝试进一步阐释“有尊严地死”的诉求时,就会发现上述不同意义上对尊严死的理解皆具有伦理的合理性。而且,这种混淆的运用也符合人们的道德直觉。
首先,从其本意来看,人的尊严是指人因为自主而享有的、与其他动物相比的优越性。人既是一种动物性的存在,同时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人的生命仅仅看作与其他动物生命无异的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人的生命的优越性就在于它与作为一个精神性的、自主的存在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此而言,人的生命的尊严就在于人可以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和死。
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倡导患者在具有自主能力时,对死亡进行深思熟虑的思考,事先选择死亡的方式。在生命的终末期,让患者安详地面对死亡,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医生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理念无非也是倡导在选择死亡的方式上,尊重人的自主意愿。基于此,“有尊严地死”也被视为论证“安乐死合法化”的一种进路。诚如美国生命伦理学家露丝·麦克琳(Ruth Macklin)所言,在这种语境中,尊严所指涉的无非就是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人的尊严就在于人有自主能力,可以自主决定和塑造自己的生命形态。当人们在上述不同意义上运用尊严死这一术语时,他们所强调的无非就是对人的自主性的尊重。因此,只要能够确保这些措施的实施是患者真实的自愿选择,它们就都能够被合理地称之为“尊严死”。
其次,当人们在安宁疗护、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等意义上运用尊严死这一术语时,是从与自主性看似对立,却又紧密相关的另一个视角——脆弱性的视角来审视死亡问题的。人是脆弱性的存在。因为,一方面,人是一种肉身的存在,肉身具有可逝性、可朽性,肉身很容易被疾病侵染,进而消逝。另一方面,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被抛向某种关系中的存在。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幸福的实现都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很容易受到来自他人和环境的伤害。死亡是对人类脆弱性最强有力的警醒。死亡让人意识到人类自身是有限的、脆弱的、短暂的。死亡是人类的终极命运,每个人都无法逃避。
在医学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并非死亡本身,并非生命的终结,而是在死亡前被病痛折磨、尊严一点点丧失的悲惨境遇。在这种无助的生活状态下,人的脆弱性暴露无遗。通常情况下,脆弱性与无法控制和丧失力量联系在一起,脆弱性意味着自主的消减,意味着我们无力应对困境,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这种人类无法回避的终极命运要求我们给出相应的伦理回应,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承认并接纳这种脆弱性。这种承认的态度非常重要。承认脆弱性这条原则在具体的医疗实践中表现为承认医学的限度。在临终阶段,接纳死亡,淡化治疗,强调关怀和照顾,尽最大可能缓解患者的痛苦和不适。在这个意义上,尊严死的诉求是如何确保在临终阶段还能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一个人那样!
从字面上来看,尊严死是在诉求一种死亡权利。但是,当我们从自主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来审视尊严死问题时,尊严死的诉求就不仅仅是对自主决定死亡方式的尊重,更是确保患者能够有尊严地走向死亡的一种生命状态。它所关注是如何“活”而不仅仅是如何“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尊严地“死”要求一种脆弱性被认真对待的“生”和“活”。这种观念的转变启发我们在探寻尊严死的法律路径时不必再纠结诸如安乐死、医生协助自杀这样一些关于死亡权的争夺中。相反,我们完全可以从捍卫生命尊严、保护生命这样一些已经被纳入法律条文的价值理念出发,寻找捍卫尊严死的现实可行路径。每个人都将在某个时刻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死亡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命运。有尊严的生活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死亡问题。
文 | 王福玲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