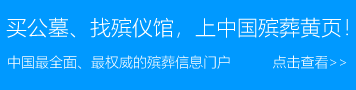妇好墓在安阳殷墟,当人们在参观游览殷墟博物馆、宗庙祭祀遗址、甲骨文考古发掘遗址等诸多景点,最后来到妇好墓时,好比从整个殷墟的宏大叙事中,突然转换视角,从宏观进入微观,通过一个历史切口,透过一位具体的历史人物,进一步解读殷商帝国的荣耀与辉煌。
走进安阳殷墟的景区大门,举目四望,位于西侧的一条宽阔大道尽头,一尊雕像特别引人注目。雕像通体洁白,远远望去,是一位威风凛凛、叱咤风云的女将军,走进端详,那威严的装束下,修长的身材,挺起的胸脯,娇美的面容,动人的眼珠里透着女性特有的温柔与慈祥。胸前左侧,女将军手握一把大钺,随时保持一幅出征的姿态,仿佛还在殷朝的猎猎大旗下,面对即将出征的将士,正要从喉管里发出气贯长虹的军令。雕像后面是一个仿古四角亭,3000年前,这里曾是墓主人的祭祀享堂,哪怕她已经故去,她的丈夫武丁以及后世殷王,除了在殷墟的王陵区祭祀先祖外,还要单独在这里隆重祭祀一位非凡的女性。亭左侧仅10米处是一个不起眼的仿古建筑,仅开了一小门。穿门而入,是一个“回”字形展厅,通过图、文以及部分实物展示表明,由于妇好墓是一座墓主身份明确、唯一没有失盗的王室墓葬,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共出土了1928件陪葬品,其中最能体现殷墟文化发展水平的青铜器共有468件,三联甗、偶方彝、大铜钺等珍贵文物相继现世,过去只停留在甲骨文中的商朝王室生活突然变得真切起来。展厅下面便是妇好墓坑,面积不是很大,墓坑为长方形,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坑里简单摆放了一些器物,墓坑四壁还有殉人的骸骨。墓坑旁边的两处藏品坑里,倾倒的器物使人想到墓主人安葬时的情景。
本来,妇好这个名字是鲜见于史籍的,上世纪1976年5月的一天,一位名叫郑振香的女考古专家带队在安阳小屯村西北角的一片高岗地进行挖掘工作。当考古队在挖掘到五米多深时发现全是硬土,再挖下去地下水就要渗出来,大部分人都准备放弃了,而郑振香却坚持继续,她认为显露出来的夯土不符常理,必须弄个水落石出,即便受到工人质疑她也还是坚持深挖。探到八米深时,铲子终于带出了令人惊喜的红色漆皮,就是这关键性的一铲,一座沉睡3000多年的殷商大墓露出真颜。通过墓中出土文物上的铭文,一个非凡的名字,一位非凡的女性,带着原始野性和文武兼备的风采,彻底颠覆人们对古代女性的认知,惊叹那远去的殷商时代,还有这样一位光彩照人的奇特女子。
公元前12世纪,衰落的殷商王朝在第20任殷王盘庚迁都后,再度兴盛。然而盘庚继任的两位殷王又黯淡下来。不过,后继的殷王小乙因为将其储君子昭放在民间锻炼,切身体会到社会底层生活,意外地做了一件光宗耀祖的大事:储君子昭继承王位后,励精图治,开疆扩土,将殷朝江山推向顶峰,他便是殷商第23代君主武丁。武丁在位时间长达59年,精力旺盛,欲望强烈,据学者胡厚宜考证,武丁的后宫王妇多达64位,儿子粗略估计也有54位。武丁时期,王妇通常要扮演配偶、助手等多重角色,但首要使命是为商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在位于殷墟中心地带的一个甲骨文书法长廊里,细细品读中国汉字的原初涵义,不得不被古人强烈的生命繁衍意识所折服,众多的古文字,或者说古人要优先创造这些古文字,很多都是对人的生、老、病、死、祖先崇拜、子嗣延续等重大问题的形象化思考,每一个古文字无不凝聚着古人卓越的精神创造。细细品味这些古文字,怀想古人强烈的生命渴望和江山永固的执着梦想,再读殷王武丁对妻子妇好生育问题的关注,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和感受。比如武丁迫切希望妇好能为他生下一男半女。不料同房了许久,妇好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武丁很着急,让贞人宾卜了一卦:“丁酉卜,宾贞:妇好有受生?”(《甲骨文合集) 13925正)贞人宾占卜的结果很吉利,妇好已经怀上了。贞人般不想让好事都被死对头占去,也来凑一脚,占卜说武丁之父小乙会保佑妇好的。武丁为此兴奋不已,但很快他又对妇好及肚子里的“龙种”忧心忡忡,有条卜辞上说:“丙申卜,觳贞:妇好身弗以妇死?”(《甲骨文合集》101360)这是武丁担心妇好和胎儿出了意外,让贞人彀占卜了一下。终于熬到分娩之日,武丁的神经又紧绷起来,命令贞人彀占卜妇好的预产期及婴儿性别。很显然,武丁迫切希望妇好产下男婴,以继承王位。卜辞中有关妇好生育之事多达三十余条,而且绝大多数由贞人彀负责占卜。卜辞中,占卜妇好分娩的月份有五次,时间分别是一、二、四、五、十月,这不可能是同一次生育的贞问,至少应有三次生育。其中有一次产下一女,可惜女婴死于难产。或许是这次悲伤的意外给妇好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损害。妇好精神恍惚,经常做噩梦。武丁非常忧心,为她多次贞问。占卜的结果是武丁之父小乙的魂灵作祟,降灾祸于妇好。妇好长期征战,积劳成疾,终于故去。有暗示妇好死去的卜辞:“贞:妇好不其死?”(《甲骨文合集》170630)
当然,作为武丁的首任王后,妇好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做夫君的生育工具,其最让人称道、也最让后人敬仰的是她突出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自古以来,战争永远不会让女人走开,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断闪烁着花木兰、梁红玉、穆桂英等巾帼英雄的美名,相比之下,早在3200年前,一个妇好便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些后继者们的榜样。妇好墓中曾出土了两把铜钺,两大两小,上半部刻着“妇好”二字的铭文。两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八九公斤。这两把巨大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铭刻在上面的“妇好”二字则显示了她在军事方面至高无上的权威。根据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表明,妇好多次受命征战沙场,前后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二十多个小国,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妇好的军旅生涯当中,最精彩的一次是和武丁一起征伐巴方的战斗。巴方位于商朝西南,时常和商发生战争。一次,武丁亲自率兵作战,战前他与妇好议定计谋,让妇好率兵在巴军退路方向预先出击,武丁自己带领精锐部队去偷袭巴方军营。巴军遭到突然打击惊慌失措,还来不及作战就四散逃走。恰在此时,妇好指挥伏兵迎头杀敌,结果巴方军队全数被武丁和妇好歼灭。这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次“伏击战”。最出名的一仗当属征伐羌方一战,“辛巳卜,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羌。”这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出兵最多的一次战争,这是一次大规模战役,这次战争的最高统帅就是妇好,也是武丁时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当时,久经沙场、战功累累的禽、羽等武丁爱将,都归妇好率领。妇好带领所属的三千人马及其他士兵一万人去征伐遥远的羌方,一万三千人几乎是当时商王朝一半以上的兵力,战争之后,羌人势力被大大削弱,且俘获大批羌人,商之西境得以安定。然而,此次胜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对方的军队,经考古专家研究,是曾经先后灭掉了三个古文明的雅利安人,并且拥有先进的武器,他们进入印度后制定出种族隔离(种姓制度)或种族灭绝制度。有学者认为,一旦商朝打败,中华文明就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沦为古印度一样。因此,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李济先生直呼其为中华民族的保卫战,才使得中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唯一没有断层的国家。如果站在人类文明史上考察,妇好伐羌之战,不仅仅扩大了殷商的版图,更为中华民族的血脉延续创下了不朽功勋。
妇好不仅是能征善战的常胜将军,她还是一位女政治家,一位拥有神权的最高女祭司。殷人信奉鬼神,凡事都要祭祀和占卜,几乎所有国家大事都要反复占卜,祈问鬼神。由于祭祀是沟通天地鬼神的重大活动,主祭者既要拥有特殊身份,又要有特殊的本领,甚至还要有特殊的语言“巫咒”,特殊的动作“巫步”或“巫舞”,善用特殊的音乐“巫音”,这些“巫咒”、“巫步”、“巫音”等言行手段,称作“巫术”。说到古代“巫术”,现代人很容易将其与愚昧落后划等号,但在人类文明史上,“巫术”却是极其重要的政教手段之一。追溯当今儒家思想文化的根源,其大致路径竟然是由巫到礼,由礼而治天下。孔子一生信奉周礼,其临终时坦言,自己是殷人之后。其创立的儒家思想,直接来源是周代礼制,若往前追溯,还是来自于其远祖的“巫”。著名哲学家李泽厚先生在分析古人的祭祀行为时认为,“甲文显示商代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都有祭祀占卜,或者‘殷王一年之中平均两天就要祭祖一次’,而且是配以天干地支即当时的天文历法知识来有顺序、有规则地进行。这意味着,‘祭’开始不同于原始人群非日常生活的巫术活动,而成为君王及上层集团几乎每日都必须进行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围绕着对祖先神的天天祭祀的仪式和占卜,便正是‘礼’的开始。‘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礼记·祭统》)。通由‘祭’,原始人群的巫术活动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图腾崇拜和禁忌法则,开始演变成一套确定的仪式制度,它由上而下日益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人群必须遵守的规范制度”(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第42页 )。因此,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妇好曾经担任过殷商最高女祭司这一角色,就会想像到,其受夫君之命,在神圣的祭祀大典上,以“超人”的能量,通天入地,教化百官乃至万民,是何等的威严,又是何等的神圣。同时,由于商朝祭祀的种类有很多,祭天、祭祖先、祭泉水,还有为了去除疾病和灾祸,以及出征作战前的祭战等等。妇好在祭祀中,她会用酒,也会用火。会屠杀牲畜,也会屠杀俘虏。根据卜辞推断,她曾因国家发生可怕的瘟疫,受武丁之命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祀大典,其中包括杀人的血祭。殷人祭祀时,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占卜活动。殷人占卜,通常把清洗干净并晾干的龟甲用火烧炙,使龟甲兽骨烧裂出焦纹。占卜人根据焦纹的纹理判断凶吉,决定成功与否,并将占卜的结果和发生后的情况刻写在同一块甲骨上,形成卜辞。由此可见,妇好不但地位特殊,战功显赫,可以主持祭祀、诵读祭文,还可以刻写甲骨文字,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是一位地道的文武双全的才女。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非凡的女性,命运对她的安排也会极其不公。从甲骨卜辞看,妇好33岁就去世了。妇好是因为什么原因去世的?从甲骨卜辞判断,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战死,二是难产而死。据甲骨文中记载:“出贞……王……于母辛……百宰……血。”这可能说明,妇好是因为血光之灾而死,或者是作战中身亡,或者是旧伤复发而逝。夏商时的战争,多是规模性的械斗。妇好经常东征西讨,想要不负伤,恐怕不可能。在那个没有医疗保障的年代,负伤之后,无法自愈,只能任由伤情恶化。从墓制较小、没有墓道分析,妇好可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匆忙下葬的,这也说明妇好是突然而亡的。在妇好死亡多年之后,武丁在一次祭祀中祷告:“马上就要与敌国开战了,请妇好在天国一定要现身显灵,保佑我们大获全胜。”似乎这场战争是一场复仇之战,复仇的对象似乎就是杀害妇好的元凶。说妇好是难产而死,根据是:甲骨卜辞中记载:“妇好要分娩了,不好。三旬又一日,甲寅日分娩,一定不好。女孩。”从这条甲骨卜辞分析,妇好因难产而去世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妇好去世后,其庙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尊称她为“母辛”、“妣辛”、“后母辛”。武丁为表示对她的深切怀念,不仅把她安葬在自己王宫的旁边,还不让她在阴间寂寞,3次专门举行祭祀仪式,焚香祷告,祈求成汤等商朝的三位先王在阴间迎接妇好,精心照顾妇好。随后又册封了一位新王后——妇妌。
由于妇好的英年早逝,她儿子的前程也受到极大影响。妇好为武丁所生的长子子渔,又名“孝己”。子渔刚出生时,武丁兴奋之余将其立为储君。随着年岁增长,子渔聪明伶俐,性格善良,恪守孝道,更是殷商未来的理想君王。但后来子渔不明不白地被贬出宫,直到抑郁而死,这让人不难想象自古以来后宫的残酷斗争。此事见载于《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殷商宗有贤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后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这里的“孝己”指的就是甲骨文中所记的、妇好的孩子子渔。这里的“后妻”当然指的是妇妌。由于妇妌在后宫斗争中获胜,他的儿子祖庚便成为殷王武丁的继任者。这一权力更替,表现在考古发现中,便是“司母戊大方鼎”和“司母辛方鼎”的大小之别。闻名天下的“司母戊大方鼎”出土于殷商的王陵区,其体量和规格均远大于非王陵区出土的“司母辛方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妇妌墓中的祭品,“司母辛方鼎”是妇好墓中的祭品。“司母戊大方鼎”之所以大于“司母辛方鼎”,很大程度上是妇妌的儿子祖庚继任为殷王后的举动,当然也不排除殷王武丁尽管之前特别钟爱妇好,但人既离世,新王后妇妌能够在后宫斗争中获胜,也必然有让武丁独宠的招术,以致于在武丁任上抬高妇妌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世道沧桑,变数无穷,曾经的宫廷斗争以及局中人的命运转折均不过是过眼烟云,即便妇妌在后宫斗争中获胜,她本人也享受到死后的荣恩,被厚葬在殷墟的王陵区内,却万没想到会遭到盗墓贼无所不能的毒手,殷墟的王陵区内,那些企图死后还要享受荣华富贵的帝王将相们,其地下幽梦无不被盗墓贼彻底粉碎。倒是妇好墓因为不在王陵区,况且墓地上面还建有享堂,某种程度上对妇好墓起到了极大的保护作用,从而躲过了身后的劫难,妇好不仅在地下安眠了整整3000多年,还意外地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妇好提供了最强大的实物支撑。妇好,这位杰出的古代女性,在殷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因为被发现而获得重生,并被后人塑像,重新站立起来,供人们凭吊,朝拜,遐思,妇好,成了殷墟地面上惟一享此殊荣的幸存者和幸运者。(蚌埠市民政局党建办 魏诗文)
寻访妇好墓的沉思
| 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