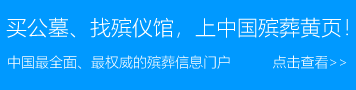每年9月,在东京湾会举行一场热闹的博览会——EndEx(临终服务与墓葬博览会)。该展会主要展示与殡葬仪式有关的服务和设备。许多展台都布置得十分精致,工作人员分发小册子和资料,有些展台进行演示或表演。除了能够发光的LED墓碑、精雕细刻的骨灰坛,还有售价几千美元的能够诵经超度的机器人,更有甚者提供用火箭把骨灰送进太空的服务。展会的氛围轻松而诚挚,甚至带有一点戏谑。据对日本殡葬市场进行调查的整个过程中,我发现,戏谑和死亡似乎并不冲突。——人人需要一个体面的葬礼——近年来,总能听到一些日本朋友、同事说起如何安排后事的焦虑。不只是老年人和中年人,甚至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也常常苦恼于此。出于这种好奇,于是,我开始了对日本殡葬产业进行了分析和研究。采访了一些殡葬服务公司经营者以及相关政府管理机构;参观新式公墓;随佛教僧侣在盂兰盆节举行悼念仪式;甚至与清理小组一同在现场处理孤独死者的遗物。通过深入了解日本殡葬文化的传统可知,日本殡葬文化深受本土神道教与外来佛教的影响,二者对日本人的殡葬观念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幕府时期,父系宗谱原则的形成奠定了日本墓葬传统的基础。1603年,幕府将军颁布法律,强制要求所有家庭必须以宗族为单位,在家乡的佛教寺庙进行登记。自此,每个家族都拥有了专属的祖先墓园。家乡寺庙负责为死者主持葬礼,而家族亲属则承担起维护墓园、祭奠祖先的职责,并定期向寺庙缴纳管理费用。1898年,新《日本民法典》颁布,进一步巩固了父系家族墓园制度。该法典规定,所有居民必须按照父系姓氏在族谱中登记,死后以家族姓氏埋葬于家族墓园。在近代日本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这一制度犹如意识形态的坚固堡垒,有力地维系了当时社会秩序中的等级与规范。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日本社会在二战战败后发生了深刻变革。1947年民主改革推行,民众的身份认同逐渐向个人主义转变,坟墓的意义也随之发生转变,从传统的祖先崇拜场所演变为个人的长眠之地。到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迎来腾飞,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家庭结构也从传统的大家族模式向小家庭模式转变。在此背景下,位于乡村社区的祖先坟墓因缺乏维护而逐渐荒废。进入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增速放缓,生育率持续下降,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2005年,日本死亡人口总数首次超过出生人口,且此后这一差额逐年递增,给日本社会带来了诸多挑战与影响。据报道,2024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首次突破29%,创历史新高,占比为29.6%,约3569.3万,其中75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超过50%。显示出老龄化加速趋势。
这意味着,“如何、由谁、在哪里” 安置死者,已成为当下日本老年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人类在新石器时代便已萌生出悼念逝者的行为。长久以来,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以仪式缅怀死者,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在黑格尔的哲学视野中,为死者建造房屋,是人类符号创造历程的开端;社会学家涂尔干则指出,仪式是人们为确认超越个体生物性存在或有限自我的意义,而精心设计的活动。在他看来,仪式宛如一股强劲的电流,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循环流转,维系着彼此的联系。由此可见,“一场体面的葬礼”早已深深镌刻在人类的文化基因之中,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在日本的传统观念里,人离世32年后,灵魂便会融入祖先之灵的怀抱。然而,在这32年期间,倘若逝者的坟墓无人祭奠、无人照管,便会被迁入无缘公墓,其灵魂也将化作孤魂,在世间孤独飘荡。当下,日本正面临着社会老龄化与无缘化的严峻现状,“为自己妥善安排后事”已然成为越来越多日本老年人的坚定信念与实际行动。在此背景下,正如文章开头提及的殡葬博览会以及各种新颖的替代方案应运而生,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善后中心(Ending Centre)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诞生的一个殡葬互助组织,与此同时,它还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词汇——“墓友”。善后中心的成员,大多是城市中的独居老人,或是没有后代的老年夫妻。他们只需支付一定的费用,便可成为该中心的会员。中心会定期组织聚餐和座谈会,为成员们搭建交流的平台,让大家彼此相识、结为朋友。当成员离世后,中心将全权负责处理一切葬礼事宜。成员最终会与生前结识的墓友,或是自己心爱的宠物一同安息在樱花树下的公墓之中。每年特定节日,工作人员还会联系佛教寺庙的僧人前来祭奠,让逝者得以安息。80岁的竹山女士便是这一组织的成员之一。她年轻时与丈夫离婚,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女儿抚养长大。竹山女士希望能在生前就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得妥妥当当,不给女儿增添任何负担。于是,在参加过几次善后中心组织的活动后,她毅然注册成为了会员。不久前,她的猫离开了人世,如今已在樱花墓园静静等候着她。能够与自己心爱的宠物以及生前结识的墓友长眠于此,让竹山女士内心充满了安全感与平静。——自动化公墓——如果说善后中心的樱花公墓多少联结着日本传统文化,那么自动化骨灰安置所(Automated Columbarium)则展示了这个国家赛博朋克的一面。“一行院”(Ichigyōin)是位于东京信浓町的佛教净土宗寺院。该寺院下辖一座自动化骨灰堂,兼具骨灰存放与吊唁功能。该骨灰堂由日本著名建筑师畏研吾设计,极具艺术美感。▲在一行院的室内吊唁厅部分,有一排整齐的黑色墓碑,每一座墓碑前都摆放着鲜花,点燃着电子香。每个墓碑之间由屏风隔开确保隐私。当接收到探视者的请求后,传送系统会将逝者的骨灰盒送到其中一座墓穴中,刻有逝者名字的一侧向外,旁边的电子显示屏会出现逝者的信息。
在室内吊唁厅部分,有一排整齐的黑色墓碑,每一座墓碑前都摆放着鲜花,点燃着电子香。每个墓碑之间由屏风隔开确保隐私。当接收到探视者的请求后,传送系统会将逝者的骨灰盒送到其中一座墓穴中,刻有逝者名字的一侧向外,旁边的电子显示屏会出现逝者的信息。当吊唁结束后,传送系统又会将骨灰盒送回骨灰存放区。这种自动化公墓传送系统的设计者大福公司(Daifuku)最初为丰田汽车生产线设计高效传送系统。20世纪9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老龄化加速,大福公司将业务转向了殡葬市场,并在1996年设计出第一套自动化骨灰堂传送机构。这样的自动化公墓目前在日本超过30家,最大的一家储存着12000件骨灰盒。除了城市土地紧张等现实因素,这样的机械化公墓又是如何被日本社会从情感上所接纳的?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完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艾莉森《另类善终》(BeingDead Otherwise )一书才豁然开朗。作者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亡灵—泛灵论”(necro-animism)。在战后日本的后工业社会语境下,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一种融入现代日常的万物有灵论。泛灵论深深根植于日本的传统世界观中,认为人类可以通过各种生命形式与神、鬼、怪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艾莉森2006年对日本玩具与游戏产业的研究呈现了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泛灵论世界观的另一种形式。20世纪90年代,机械怪兽类动漫及其衍生玩具,例如《数码宝贝》(Pokemon )和电子宠物,在青少年甚至成人之间大为流行。在一个充满了沮丧和不确定的时代,“失落的一代”通过这些“口袋里的怪兽”重新获得想象世界的方法,治愈和修复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失去的和被剥夺的联结。如今,这种万物有灵世界观延伸至殡葬产业。在技术与墓葬结合的过程中,自我与他者、人类与非人类、人与物的界限都在变得模糊。艾莉森将这一结合称之为“社会的假肢”——在一个日渐无缘化的社会里,殡葬的意义不断衰退的今天,技术代替人类照护逝者,维系社会的纽带。在呈现并分析了当代日本关于殡葬的各种新形式之后,艾莉森坚持认为,尽管诵经机器人或是自动化公墓为眼下的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但照护死者灵魂的意愿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依旧非常重要。拒绝“逝者之死”,在生命世界中继续为他们留出一席之地,或许是人类社会的根系所在。(完)